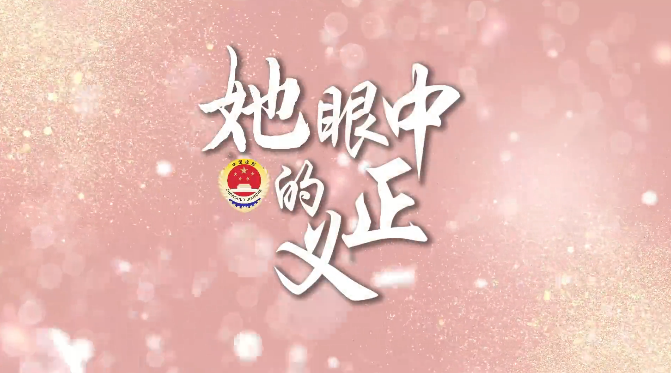对于个人信息的保护,实际上就是规范个人信息收集、整理、修改和加工、保存、使用的各个环节。这其中既包括一般性的原则,同时又有关于信息权利主体、义务人以及权利范围方面的规定。我国台湾、香港和澳门地区相关的个人信息保护法规由于制定时间与具体制度环境的差异,对于上述方面的规定不尽相同。在个人信息的一般保护原则方面,我国台湾地区《电脑处理个人资料保护法》第5条规定:“个人数据之收集、处理或利用,应尊重当事人之权益,依诚实及信用方法为之,不得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范围,并应与收集之目的具有正当合理之关联。”实际上规范限制了收集个人信息的目的、处理和使用。香港《个人资料(私隐)条例》规定得更为详细,其对于资料的收集、保存、使用、保安、提供和查阅规定了所应遵从的6项原则,包括资料收集的合法、公平,资料披露和保存的时间限制,使用合乎目的等。澳门《个人资料(数据保护法》第5条、第6条、第7条对个人资料收集、处理、敏感信息的处理都明确了规范。其中第5条对资料收集规定了5项原则:方式合法,目的正当、特定、明确,范围适合、适当不超越处理数据的目的,准确,保存符合目的所需期限。从世界范围看,目前最具影响力的个人信息保护原则当属1980年9月23日由欧洲经合组织发布的《隐私保护与个人数据信息国际流通的指针建议》,该建议规定了8项原则,分别是限制收集原则、完整正确原则、目的明确原则、限制利用原则、安全保护原则、公开原则、个人权利原则、责任原则。对照之下可以看出,台港澳地区相关个人信息保护法规不同程度地体现了上述原则。而全国人大常委会2012年12月制定的《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也显示了上述原则的影响。

公众知情权与个人信息自决权的平衡
从立法的视角看,法条尽可能制定得清晰准确,明确各自的权利界限,保护范围和救济措施,这可以在相当程度上避免信息公开与个人信息保护之间的紧张关系,但是在实践中依然不能完全避免两者间的冲突。比如“公众人物”的个人信息公开问题,出于“公共利益”考量的个人信息强制公开等如何界定等问题,这类问题的解决就需要更具操作性的理据。法律面对相互冲突的权利时,通常的做法是进行法益衡量。前面已就个人信息的权利属性做了界定,接下来的问题是,信息公开的权利基础又是什么?台湾地区2005年12月28日通过的《政府资讯公开法》共24条,其中第1条就明确规定,“为建立政府资讯公开制度,便利人民对公共事务之了解、信赖及监督,并促进民主参与,特制定本法”这一条清楚地表明我国台湾地区信息公开的权利基础是“人民知的权利”,对于这种“知的权利”的界定,我国台湾地区学者以“宪法”权利为理据。大陆一般称其为知情权。香港和澳门地区虽然没有直接在相关的信息公开法规中规定政府信息公开的权利基础,但是从其条文的具体规定不难推知其预设前提是公民的知情权,香港地区有时称其为资讯权,澳门地区称其为信息权,实际上是同一概念。有大陆学者认为政府信息公开即是为了实现公民的知情权。而有学者进一步将知情权归于宪法言论自由权的延伸,或是人民主权的体现,或是宪法监督权的引申。这些主张与我国台湾地区学者的主张颇有异曲同工之处。由此,从权利冲突的视角看,信息公开与个人资料保护之间的紧张关系就转化为公众(公民)知情权与公民个人信息自决权之间的平衡问题。从大陆与台湾、香港、澳门地区的相关法律规定看,解决上述权利冲突应遵循以下原则:
(1)权利平等原则。
与法律体系不同,权利体系没有位阶关系,原因是如果赋予某种权利在社会意义上优于其他权利,就等于赋予该权利主体以特权地位,这实际上违背了权利主体平等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原则。
(2)公共利益优先原则。
当公权力范畴内的知情权(知的权利)与个人信息自决权冲突时,应采用社会公共利益优先的原则,比如大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14条规定:“行政机关不得公开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但是,经权利人同意公开或者行政机关认为不公开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可以予以公开。”台湾地区《政府资讯公开法》第18条也有同样的规定,香港《信息公开守则》中也有类似规定。
(3)平衡协调原则。
当私权范畴内的知情权与个人信息自决权冲突时,应兼顾两种利益的平衡,对两种利益进行协调。
(4)人格尊严原则。
新闻采访、创造、出版等必须涉及特定个人的隐私时,不得以伤害其人格尊严为目的,否则负侵权责任。这一原则对应于美国法律关于诽谤认定的实际恶意原则。
(5)权利救济原则。
即允许个人资料权利人就是否公开进行行政复议或寻求司法救济,以避免作为强势一方的政府单方面作出不利于相对人的决定。